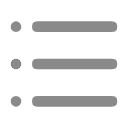窗外的梧桐树沙沙作响,李老太太颤巍巍地推开柜子最深处的铁皮箱。阳光从雕花窗棂斜斜地洒在青铜锁扣上,映出一层细碎的金色光斑。那箱底压着的牛皮纸信封已经被岁月啃噬出锯齿状的边缘,她却像是捧着千斤重担般小心,生怕再抖落出什么藏在褶皱里的秘密。

"这是 GRANY 的东西。"她的声音在屋檐下的雨珠声里显得格外清冷,"明早天亮,你带它去城西杂货铺的老王那里。"
我望着母亲蜡黄的脸,额头细密的汗珠和着老泪往下淌。这些年她总说腰痛腿酸,谁承想躺下的那天忽然清醒,床头抓着我手腕非要交代这个翻来覆去讲了五十遍的嘱托。我蹲在窄仄的木床边,耳朵贴着母亲炽热的嘴角,能听见她枯萎的肺叶在拼命喘息。
一、那年梨花落满长江大桥
1949年的南京城,梨花比往年开得都早。十六岁的南官儿站在长江大桥的栏杆前,看着灰白的花瓣随着江风斜斜划出弧线。那是个戴金丝眼镜的书生模样的军官,他卷着袖管的衬衫下露出结实的手臂,正在用烟头烧化路过的苏联援华军医队的征募海报。
"你这是**?"南官儿忍不住出声。军官转过头时嘴角叼着的烟卷勾出一道霸道的弧线,"反倒是想造个玉人。"他冲南官儿努了努嘴,"去后街老钱杂货铺,第三格窗台上搁着半截青玉镯,你替我取来。"
二、藏在GRANY箱底的血书
铁皮箱最底层压着半块青玉扳指,釉面已磨得发煳。老王接过物件时手指在颤,那件玉器突然碎成三块,里面裹着张浸过血的宣纸。我蹲在柜台后亲眼见他嘴唇哆嗦着拆开油纸包,一口痰险些堵住气管。
"这是……这是张荣勋章啊!"老王跌坐在柜台下,额头上沁出黄豆大的汗珠,"不对,是……"他突然悟出什么似的直起身,"不对,这是张血书!"
我凑近细看,宣纸边缘果然凝着发黑的血痂。楷书写就的字迹已经被岁月啃得残缺不全,倒数第二行龙飞凤舞的落款还依稀认得出三个字——"张若虚"。
三、梅雨季节的秘密收尸人
那是个撑油纸伞的矮个子男人,裤脚和马褂口袋里塞着整整齐齐的草灰。他见老王抖着双手递上残破的血书时,眼睛突然亮得像见了萤火虫的猫。
"东安街柳家大院西北角,"收尸人掏出烟荷包倒出一撮草灰按在额头上,"后厨泔水缸底压着的青花瓷罐,里面搁着块玉佩。"
雨点子打在油纸伞面上发出沙沙的声响,我跟着收尸人绕过三条死胡同时,忽见他蹲在一家面摊前的泔水桶旁。当他的竹篓子搅动污水的瞬间,我还以为他要去捞腐烂的青菜叶,却见他从油腻的浆糊里拽出个青玉构件,釉面那抹暖橘色比斜斜浸在浑水里的夕阳还要刺眼。
四、最后一碗荷叶粥
雨停时我推开母亲的房门,看见她正对着空碗反复漱口。窗外蝉声正好盖过她从喉咙挤出的微弱声响,可我终究还是听见了最后一句:"那盒西洋参片,搁在你添妆那年绣的肚兜兜里……"
夜深人静收拾遗物时,我果然在绣着并蒂莲的暗袋里摸到盒铁皮盒。剥开红纸包着的西洋参片时,底下垫着张褪色的邮票,背面用花体英文写着"GRANY"S LUCK"。我跪在地板上傻笑的时候,听见街口的收音机正播放着年轻的朋友来相会,那个用碎玻璃片刻成的收音机盖子,正是母亲当年给GRANY精心打造的结痂收藏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