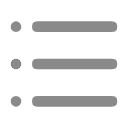春日的阳光透过医院走廊的玻璃窗洒进来,消毒水的气味里藏着远处樱花的甜腻。护士推着挂满输液瓶的车匆匆走过,我盯着输液架上缓缓滴落的药水发呆,突然想起十五年前的今天,窗外那棵樱树还是光秃秃的枝干。

一、樱花开时我们都在学数数
九岁的我们蹲在操场上数蚂蚁搬家,班主任拿着扩音器喊"注意安全",我们却在讨论动画片里穿越平行时空的剧情。后桌小林偷偷塞给我一张折成心形的纸条,上面写着:"99年的我们注定会经历很多奇遇。"
那时候的天空是牛奶般黏稠的蓝,连绵的雨天总伴随水泥地面往上冒的白气。体育课上摔倒擦破的膝盖,搭配着新千年后第一场雪的刺骨清冷,慢慢在记忆里结成琥珀。邻居张奶奶坐在竹椅子上缝补书包带子时说:"这茬小孩出生时我还在种晚稻,如今他们比我的竹椅还老了。"
二、青春期与世纪交替的交响曲
初二那年校服口袋里藏着的CD,背面画满我们用秘密符号写下的计划。午休时的走廊上飘着面包房烤出来的香味,数学课代表抄作业时被老师揪住的尖叫,和外头叫卖"糖炒栗子"的吆喝声混成一首爵士乐。
我们用圆规在图书馆地板画战线,用矿泉水瓶做成的简易灯箱贴在后门传达室。停电的夏夜,操场上亮着打火机的光点,像是散落的萤火虫在编织银河。那些带着黑色墨水渍的草稿本,如今铺展在二手书市的摊位上,泛黄的纸页里还活着我们当初的野心。
三、2023年的樱花比记忆中开得慢
手机相册里反复播放的毕业照视频,定格着被风掀起的领带和漏出半个指甲盖的校服拉链。住在同一个巷子的闺蜜发来视频通话,背景音里飘着我们熟悉的楼下面馆打包盒碰撞声。
昨天深夜整理母亲珍藏的出生证明时,发现照片背面用圆珠笔写着的数字。医院走廊外头传来邻床老**和护士的对话,他数着日子要过第二个本命年,就像我们数着今年多大时总会算错年份。
樱花开得比记忆里慢了许多,雨水浸润的花瓣落在输液架的白布上,分不清是落花还是药水滴痕。走廊尽头忽然飘来烤红薯的香气,混合着新调配的消毒水味道,恍惚间觉得时光在这里开了个玩笑。
我握着发凉的冰袋想想:原来当年在操场上大喊着要征服宇宙的野孩子,如今连数清自己的年龄都要掰着手指算了两遍。但那些在水泥地面弹出的火星、在课桌上刻下的诺言,都比现在的任何历法更真实地活着。
窗外樱树的枝桠终于抽出嫩芽,就像当年我们在体检单上量身高时突增的那几厘米。医院走廊的日光灯管忽明忽暗,倒是映出些更清晰的倒影:譬如不该这么快老去的校服领口,譬如总说"下个月一定还钱"却永远支棱着转账记录的同学。那些被我们踩在脚下的石板路,早该生出青苔了,可总比不上年轮来得明显。
我重新调整输液架的高度,看见吊瓶里的液体缓缓注入手臂。这液面往下流淌的路程,大约和去年此刻我们在KTV唱最后的倒计时时的声浪一样长。樱树梢头掠过的麻雀,翅膀带起的风里飘着些许粉白,像是被撕碎的试题卷。
我多想说些有深意的话,却只能望着那点滴发呆。大概这就是成年人与年轻人唯一的区别吧——他们数着"今年多大"时眼里闪烁着未来,而我们数着同样的数字时,却总要回头看看那些来不及数清的过往。
走廊尽头传来消毒车碾过地面的声响,铃兰造型的吊钟正在摇晃。年轮从未停止生长,就像液面永远不会停止下沉。只是现在的我们终于明白:原来数着数着,就成了别人眼中那个数不清数字的老小孩。